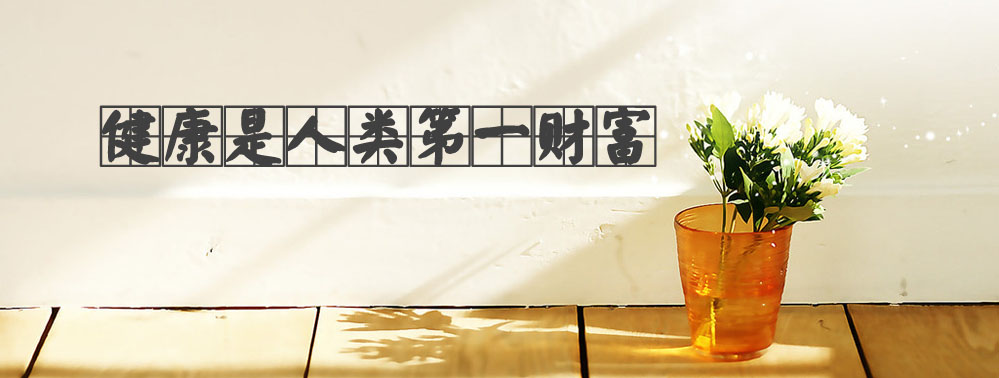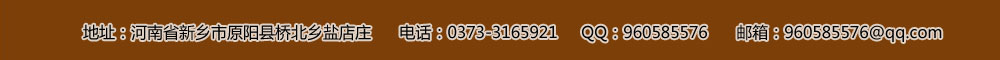胡大一大医要有大情怀
前段时间,我读了陈旭岩的《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其中有两个故事让我十分揪心。文章中提到,有一位十几岁的患有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男孩和一位患有重症急性胰腺炎的32岁女患者,他们都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放弃治疗。女患者的父亲无奈地说:“我们不治了,回家吧。”当家人抬起女患者时,她使劲儿抓着病床的栏杆不撒手,让目睹的医生永难忘记。
医院工作时,接受的最基本的教育就是敬畏生命。但是,在社会发展转型的时期,医院的运营机制变得“功利”了。现在的医疗技术水平可以让患者起死回生,如冠状动脉介入技术,挽救了大量濒临死亡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但是救治的效果还要取决于开始的治疗、开通心肌梗死相关血管的时间等。医院接诊患者时总是先问患者有没有医疗保险或有没有钱,才能决定是否为患者进行最优化的治疗方案。先交钱,后救命,钱没交上就不做手术。这种状况实在让我忍受不了。这种做法从根本上颠覆了从医的良心与道德底线。我们一直在讲生命重于金钱,而现在却成了金钱重于生命。每当我谴责这种现状时,我的同事都很无奈。因为患者欠了医药费,院方会直接扣所在科室负责人和当事人的奖金。
陈旭岩在他文章中说:“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或许只是当下我们各行各业转型时的一种必然经历。在种种冲突困扰之中,我们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他讲的更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文章的标题,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
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式下发的文件中也提到,要求医疗机构对危重急诊患者,可以先救治,后付费。这是中央政府部门发出的明确信号,应令行禁止。尽管落实这一代表正能量的要求还需要时间,但是这毕竟是向正确方向推动医药卫生改革的重要举措。
几年前,我从报纸上也看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对交通事故创伤的患者进行先救治后付费的应对机制,一是明确以区域医院,就近抢救;二是由公安、交通、卫生等相关部门设立赔付基金,医院能够先救治患者。
年,医院心脏中心开通了抢救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真正实现了先救治后付费的模式,医院并没有因此亏损。急性心肌梗死是要命的病,医生需要尽快开通心肌梗死相关的病变血管的一个支架,用价廉的裸金属支架与最贵的药物洗脱支架,在救命效果上并没有统计学数字讲的那么大的显效差别,况且,年还没有广泛运用支架技术,主要是利用球囊进行扩张血管。当时,球囊是允许重复使用的,但是从未因重复使用导致患者出现过感染或并发症。年,医院担任心脏中心主任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通绿色通道。我向院领导汇报我的想法后,主管经济指标的副院长质疑我:“欠费了咋办?”我回答:“心肌梗死是要命的病,并且开通一个血管救治费用并不高。无论有无公疗保险或医疗保险的患者,只要全力救治、沟通好,我不敢担保无一例欠费,但是大多数患者与家属应该都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只允许试行一个月,果然没有欠费的现象。
由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需要植入支架,医院和科室带来利益,包括首都在内的一些城市,出现潜规则运作,用现金买卖患者的“黑市”。本应承担院外现场急救与有序转运患者的急救中心也建立了心导管室,开展了支架手术。最能体现支架价值的救治也被金钱价格化了。只有建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公平可及的体制,建立患者利益至上的价值体系与职业精神,建立健全院外急救系统、医院急诊、影像、心血管内科等各相关科室协调联动模式,植入支架技术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这里就涉及了医生的人文精神、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以患者为中心的高效协作模式。
社会转型期出现一些丑恶现象很可恨,但并不可怕。医务人员会在一个时期感到痛心又无奈,但是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不能麻木,相信一切危害患者与公众健康的丑恶现象只能热闹一时,不可能持久的。一个医生,几个医生,甚至医生的群体在社会转型期,对上述丑恶现象的抗争不一定立即生效,但是坚持持久战,正义、公正一定会战胜邪恶。
(本文为原创文章,转载需授权并标明来源“医药卫生报”)
北京看白癜风的医院有哪些西宁治疗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