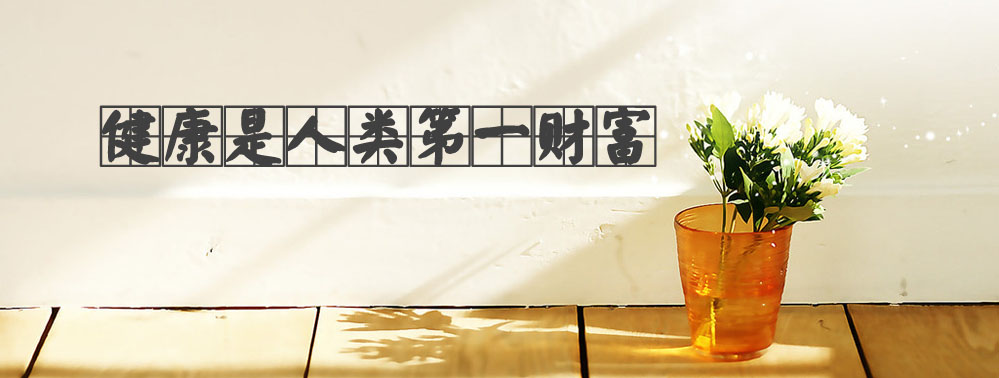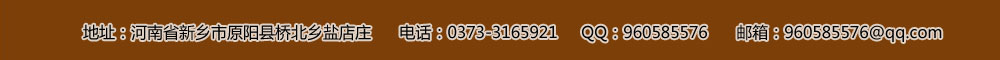重症胰腺炎合并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血
本文原载于《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年第4期
患者,男,54岁,农民,因"中上腹胀痛半天"于年9月18日入院。入院查体:体温(口)37.6℃,脉搏次/min,呼吸23次/min,血压/76mmHg(1mmHg=0.kPa);疼痛评分为3分;神清,精神软,皮肤巩膜轻度黄染,全身体表淋巴结未及明显肿大,心肺无殊,腹膨隆,腹肌紧张,中上腹有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缘下未及,Murphy征阴性,移动性浊音阴性,四肢肌力5级,四肢无水肿,巴氏征阴性。血脂全套:三酰甘油84.41mmol/L,总胆固醇13.59mmol/L,血淀粉酶IU/L,脂肪酶U/L。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6.2×/L,血红蛋白17.7g/dL,中性粒细胞比例0.,腹部增强CT:(1)急性胰腺炎伴周围渗出积液,邻近十二指肠水肿;(2)脂肪肝,胆囊胆汁淤积,胆囊壁毛糙(图1)。既往史:年至今有3次急性胰腺炎病史,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饮酒史10余年。根据病史与实验室检查诊断为急性胰腺炎(重症、高脂血症性),收住重症监护病房(ICU)。入ICU后予以禁食,胃肠减压,抑酸及抑制胰酶分泌,纠正酸碱、水电解质失衡,补充白蛋白,灌肠通便,预防应激性溃疡,化痰,镇痛等对症治疗,亚胺培南抗感染,并行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10月7日开始患者体温明显上升,最高为39.5℃,考虑不能排除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多次血培养提示棒状杆菌属,予加用万古霉素抗感染治疗。患者入院后持续发热,10月13日经多学科讨论后行腹腔内坏死组织清除+持续冲洗引流术。一直予以亚胺培南(0.5g,静脉滴注,1次/6h),后期联合万古霉素(1g,静脉滴注,1次/12h)治疗(9月18日至11月2日),但患者仍然发热,体温在38~39℃之间波动。11月2日查腹水常规为白细胞/μL,中性粒细胞44%,淋巴细胞56%,腹腔引流液培养为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药敏结果见表1)、产气肠杆菌和屎肠球菌。复查腹部CT提示:重症胰腺炎,伴出血、坏死及大量渗出,腹腔积液,肠系膜根部多发肿大淋巴结(图1)。血常规提示白细胞5.5×/L,中性粒细胞比例0.,CRPmg/L。考虑重症胰腺炎伴腹腔感染,给予美罗培南(1g,静脉滴注,1次/6h),联合替加环素(50mg,1次/12h),抗感染治疗12d(11月3至14日),患者仍然持续高热。11月16日复查腹水常规白细胞/μL,中性粒细胞92%,血降钙素原(PCT)14.8ng/mL,血CRPmg/L,血培养为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药敏结果见表1),诊断考虑败血症(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腹腔感染,予多黏菌素E(万单位,静脉滴注,1次/8h)+替加环素(mg,1次/12h),同时卡泊芬净(50mg)经验性抗真菌治疗。11月22日下午患者腹腔引流为血性液体,血压下降,考虑腹腔出血予急诊行"剖腹探查、止血、胆道镜脓腔探查、腹腔冲洗引流术",术后继续予以替加环素+多黏菌素+卡泊芬净抗感染治疗2周,后患者体温逐步降至正常,复查血培养转阴(3次),血常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及血CRP下降转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讨论
近十余年来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Enterobacteriaceae,CRE)感染在世界范围出现并呈流行趋势,其中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和肠杆菌属细菌,这些菌株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原因是产碳青霉烯酶[1]。目前,在我国产KPC(Klebsiellapneumoniaecarbapenemase)型碳青霉烯酶菌株的传播和扩散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2]。由于这些菌株的质粒和染色体上携带多种耐药基因,可以导致菌株对所有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耐药,只有少数菌株可能对磷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多黏菌素及替加环素敏感。CHINET耐药监测显示我国CRKP的检出率从至年的≤1%上升至年的14.1%,年高达15.6%,CRKP不仅检出率上升迅速,而且所致感染的病死率高,故美国CDC细菌耐药报告中将CRE列为最高级别"紧急威胁"。目前,CRKP医院相关感染,但也有少数社区获得性感染的报道。研究认为导致CRKP菌株感染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1)既往多次或长期住院,(2)入住ICU,(3)接受过侵入性检查或治疗,(4)免疫力低下,(5)严重的基础疾病,(6)初始应用过多种抗菌药物[3,4]。本例患者基础疾病为重症胰腺炎、脓毒血症,既往有糖尿病病史、长期饮酒史及反复发作的胰腺炎病史,病情危重,入院后一直在ICU住院治疗,行2次腹腔手术处理,同时有腹腔留置管、深静脉置管等多种侵入性操作,尤其是出现长时间的碳青霉烯类(46d)和糖肽类(21d)抗菌药物的暴露。研究发现,既往广谱抗菌药物的应用如β内酰胺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甲硝唑、万古霉素、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是产KPC肠杆菌科细菌定植和感染的危险因素[4]。尤为关键的是,同时期在ICU中有感染CRKP的患者。因此,本例患者存在导致CRKP感染的多重危险因素,亦或者是先有肠道定植后再从定植转变为感染,并且从局部的腹腔感染播散至全身血流感染。
目前,对于CRKP感染的治疗包含单药治疗和联合治疗。治疗原则为尽量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敏感的抗菌药物,或选择中敏或有一定抑菌圈的抗菌药物,大剂量联合治疗[5]。联合治疗必须根据PK/PD原理设定给药方案,如增加给药剂量、延长某些抗菌药物的滴注时间等。对CRKP细菌有较好体外抗菌活性的抗菌药物主要为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碳青霉烯类、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及磷霉素对部分菌株也有一定的抗菌活性。此外,新型的β内酰胺酶抑制剂阿维巴坦对CRKP也有较好的抗菌活性。现有大部分临床资料证实联合治疗优于单药治疗,尤其是对血流感染和危重症患者[6]。Neuner等[7]报道60例产KPC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患者,体外药敏结果提示其对替加环素的MIC90为1μg/mL。Hirsch等[8]报道产KPC肠杆菌科细菌对替加环素几乎%敏感。虽然替加环素体外有较好的敏感性,但回顾性病例分析替加环素单药治疗CRKP菌株感染的病死率为0~65%,在流行地区的ICU甚有80%的病死率[9]。随着替加环素临床使用的增加,这些菌株对替加环素的MIC有逐年上升趋势[2],临床已陆续分离到替加环素耐药菌株,因此,在KPC流行地区,替加环素不推荐作为经验性治疗方案。此外,替加环素治疗成功与否与菌株的MIC值密切相关,且对于不同部位感染如血流感染、尿路感染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须考虑其有效的治疗浓度。多黏菌素体外药敏结果提示,产KPC酶肠杆菌科细菌对其有很好的敏感性。Tumbarello等[10]对株产KPC肺炎克雷伯菌的体外药敏结果提示,菌株对多黏菌素的总体敏感率为88%。但在Medline获取34个共例CRKP感染患者的研究中发现,单用多黏菌素组有较高的失败率47%(34/72),对其进一步分析提示多黏菌素成功与否与其给药的剂量密切相关[1]。多黏菌素单药治疗产碳青霉烯酶菌株感染的有效率为14%~67%,并且在治疗过程中极易出现菌株对多黏菌素的异质性耐药。因此对于产KPC菌株的感染单用多黏菌素治疗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给予合适的剂量和防止异质性耐药的发生[10,11]。
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治疗产CRKP感染必须充分评估菌株本身的MIC值,目前认为碳青霉烯类药物用于治疗CRKP感染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MIC≤8mg/L,(2)大剂量(如美罗培南,2g,1次/8h)给药,(3)延长静脉滴注时间至2~3h。而我国这些菌株对美罗培南的MIC值大部分在8mg/L以上,因此单用碳青霉烯治疗CRKP感染需谨慎,重点需考虑感染部位和MIC值[2,10,12]。本例患者首先在腹腔引流液分离到CRKP,其中替加环素的MIC为0.38mg/L,符合替加环素治疗腹腔感染的适应证。同时联合美罗培南(1g,静脉滴注,1次/6h)作为联合治疗方案,但事实上这样的联合达不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因为这株细菌对美罗培南的MIC值为大于32mg/L,根据PK/PD理论,无论增加剂量还是延长给药时间,美罗培南对菌株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事实上这样的治疗方案真正起作用的只是替加环素。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由腹腔感染最后转变为血流感染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外科引流不畅、反复腹腔出血等。CRKP血流感染往往需要联合治疗,联合治疗方案治疗血流感染的病死率为0~34.1%,明显低于单药治疗的病死率44.4%~57.8%[1,10,13]。本例患者通过检测腹腔引流液和血液这两株细菌对替加环素和多黏菌素的MIC值结果提示均敏感,但血液样本中分离的菌株对替加环素的MIC值为1.5mg/L,因此结合体外药敏试验结果和PK/PD理论最后选择替加环素加倍剂量和多黏菌素E这一联合治疗方案,最后使感染得到控制,血培养转阴性。但同时发现替加环素在治疗过程中出现MIC上升(从0.38mg/L上升至1.5mg/L),因此使用替加环素需充分考虑及监测其MIC值的变化,根据不同感染部位和MIC值调整给药剂量达到治疗目的。
综上所述,对于CRKP菌株的防治需要全方位,多因素,多途径加以干预[14]。需充分评估患者是否有感染CRKP的高危因素,其中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是关键,长时间广谱抗菌药物的暴露与CRKP感染密切相关。需根据体外药敏结果选择合适的联合治疗方案,现有的研究认为替加环素联合多黏菌素对CRKP菌株感染有较好的疗效。当然根据不同MIC值、感染部位选择个体化的抗感染药物是精准医学在抗感染领域的最好诠释。
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 无
参考文献(略)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