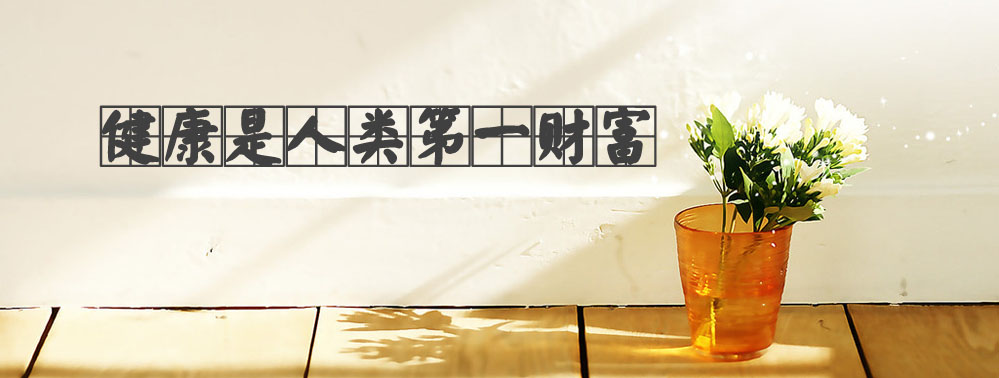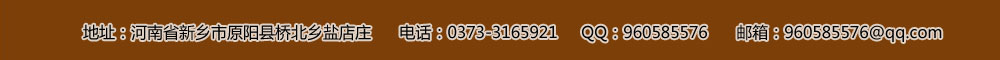最好的编剧,写不出急诊室的故事嘉
医患关系,是如今最“热门”的关系之一。急诊室,往往是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曾几何时,医生是令人羡慕、高尚的职业,如今却是人人自危的“高风险”行业。在高强度的抢救责任之外,我们还要面对病人的不信任,家属的谩骂甚至殴打,家人的担心和不理解,以及没有尽头的生离死别。
我已经在急诊这个岗位上呆了二十年了,可能嘉兴找不出第二个能坚持那么久的医生。我亲身经历了嘉兴急诊科室从起步到壮大的过程;也目睹了医患关系从信任到崩塌,再到重建的坎坷。不可否认,在生命的去留面前,如今的医疗手段仍然显得如此渺小,我也有太多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常安慰科室里那些焦虑、沮丧的年轻医生:“我们也是人,只能治病,不能治命。”但每当我亲手将一条生命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就感到一切的委屈都值得了。没想怎么捞钱,却也没想到自己进了“敢死队”
年,我大学毕业,医院。医院成立重症监护室,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发现农药中毒送来抢救的病人特别多,医院就派我到上海学习血液净化。
回来之后就去了急诊室。严格地说,那时还称不上“急诊科”。有危重病人来了,就把门诊的医生叫过来抢救。有的年轻医生不愿意来抢救,一是累,二是怕。我倒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就整天泡在急诊室。遇到一些疑难杂症,老医生都说不出来,最终被我识别出来了,就特别有成就感。所以只要急诊的电话,我随叫随到,如果他们不叫我,顿时觉得人生都失去意义了。
而且急诊经常会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医生过来,我正好趁机向他们请教一些专业问题。就这样到了年,我又主动提出来去杭州进修。在一些人看来,当初为了职称等等进修一次就够了,进修第二次简直就是个傻子。因为进修期间没有奖金,只发基本工资,更何况那段时期又是医生创收比较疯狂的时候。我没想怎么捞钱,却也没想到自己进了“敢死队”。
那次进修是在杭州,学习介入治疗,主攻心血管这一块。为了能在半年时间里多学习些知识,我几乎天天泡在CT室。时间久了,每天早上起床时,掉一脸盆的头发。原本乌黑浓密的头发,渐渐有了秃顶的趋势。所以同学们都戏称自己是“敢死队”。我们都是学医的,自然知道辐射的危害,心里也害怕自己会不会死掉。
进修结束回到单位,整个人都没力气,每天一下班就躺在床上,睡一觉再去吃饭。过了几天,我去做了一个血液检查,白细胞又升上去了,很开心,跟老师说,应该不会死了。
如果说,我在急诊的前七八年,是在积累经验,提升自己的话,那么第二次进修回来,我必须要逼自己出成绩了。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装心脏起搏器的那个病人。
那一天,一个医院,希望装一个心脏临时起搏器。我进修时看别人装过,自己可没实践过。老人意识清醒,身体尚可,医院可能也来得及。装还是不装?老人坚持就地手术。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硬着头皮就上了。
可是在手术过程中,意外突然就发生了。老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呼吸心跳全部停止。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但那么多年的急诊临床经验,使我迅速作出了反应,其他医生和护士轮流进行心肺复苏,我继续操作安装起搏器。装好后一启动,病人马上活了过来。
这一次抢救,为我的急诊生涯留下了太多经验教训。我也将这个例子讲给后辈听,告诉他们如何突破这第一关。
每天都好像生活在电视剧里,每天的剧情都不一样
空下来的时候,我也会想:把这些年急诊发生的故事写下来,就是一本书。最终一直没有落笔,因为故事实在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写起。我每天都好像生活在电视剧里,每天的剧情都不一样。最好的编剧,写不出急诊室的故事。
我们看得最多的,就是生离死别,以至于喜乐哀伤不再会轻易表现出来。常常有病人家属以此指责我们:“你们医生怎么这么冷漠!”其实看到鲜活的生命逝去,我们心里何尝不伤痛。有一位打工者只有三十岁,在工地上出事故,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过了一会,死者的妻子来了,带着只有五六岁的孩子,还有年迈的老人。早上出门还生龙活虎的丈夫,不到几个小时就阴阳两隔,再坚强的人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妻子抱着丈夫的遗体号啕大哭,不一会就哭晕在地。我们赶紧将她放在一边的病床上。等她再次醒过来,出人意料的,只见她默默地走到丈夫的病床边,一点一点地擦去遗体上的污迹,整理好凌乱的衣服,然后转身安慰公婆和孩子,没有哭声,没有眼泪,平静得有些可怕。我知道,她是此时最悲伤的人,可她心里知道,自己也是最需要坚强起来的人。还有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伴走过了六十多年的时光,相依为命。老婆婆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了。老人就这么坐在病床上,守着老伴的遗体,一动也不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忍心上去打扰他,就这么看着他坐着。过了好久,他才拿起笔,在死亡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好似用尽了他所有的生气,签完之后,他老泪纵横。
送来急诊科的病人,很多都命悬一线。留给我们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五分钟。每年我们都会收到锦旗,太多了都没地方挂。“是你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面锦旗送来不久,对方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小伙子是江苏人,在嘉兴打工,晚上回家的路上被车子撞了,飞出十几米,当场就没有了意识。医院的时候,全身多发性骨折,颅内出血,内脏也有出血,已经失血性休克,大半条命没有了。任何送来的病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组织血源,动员一切有时间的医生护士紧急抢救。小伙子的心跳呼吸停止了,要做心肺复苏,有一位护士怀着身孕,二话不说上去就按。对孕妇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很可能导致流产,这一点,相信她心里非常清楚。经过几个小时的急救,最终将伤者救了回来。他出院时,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今后可以与常人一样生活。我们经常会去福利院看望那些孤儿。人们拼命想延续自己的生命,但这些生命从出生那一刻就被遗弃了。有一个孤儿叫小球,非常乖巧可爱,不知怎么背上长了一个脓包,总是复发。于是医院,给他特级护理,大家都将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护士们给他买玩具,买吃的,每天都仔细地给他清理伤口,将里面的烂肉和脓血清洗干净。半个多月后,小球完全康复了,他走的时候,有几个护士不舍得,泪水直流。
前段时间新闻上说,嘉兴一医院里跑出来,劫持了一个陌生人,目的就是想引起别人的 现在的年轻医生往往不愿意到急诊科来,觉得太苦了。上班要从早上八点一直上到下午五点,然后第二班从下午五点上到第二天早上八点。这个月我们一共接诊了挂号病人七千八百多人,还有没挂号的病人三千多人,平均每个医生按每天坐诊八小时算,3.2分钟就要看一个病人,这还不算吃饭、上厕所、抢救危重病人的时间。诊病时间太短,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就是容易误诊。年,医院不久,来了一位离休老干部。老干部来的时候说肚子疼,之前也疼过,医生说是胰腺炎,吃了药就好了。如果医生赶时间,贪省力,很可能就仍旧按胰腺炎给治了。不过我觉得老人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就详细询问了病史,还让他去拍片确认一下。老人很生气,觉得我是故意要他多做检查,多花钱。但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去拍片了。我一看片子,果然不是胰腺炎,而是肠梗阻。肠梗阻会导致肠道坏死,严重可能致命。所以我要求那些年轻医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只看报告,有时还有点极端地对他们说:“不要相信任何人。”当然这是指病理诊断上,要有自己的想法。类似前面那样的误诊,一次两次病人也许还能接受,可累积起来,就会一点一点摧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医患信任。假如一个病人,在听到医生的诊断之后开始怀疑:“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啊?我看你不行,找你们主任来。”此时,医生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坚持自己,万一不幸出了事情,那么医生倒霉;二是保守治疗,将病医院。这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医生不敢给病人治病,病人也越来越不相信医生,然后就产生了此起彼伏的医患纠纷。有的病人满地追着打医生,警察在旁边看,帮不上忙。我现在根本无法将精力集中在专业上,各种医患调解占据了本就宝贵的抢救时间。为了保护医生,医院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今年开始在每个诊室里面安装应急铃,加强保卫工作等等。医生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又不敢回家跟家人说,怕他们担心。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建了一个QQ群,压力大了,就在里面吐吐槽,发泄一下情绪。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上电视专门做一档节目,邀请对医疗状况不满的市民,坐而论道,举办一个“辩论会”。为什么一个心脏支架出厂价几百块,到了患者身上要十几万?为什么药价迟迟降不下来?为什么有些检查看似多余却不得不做?等等这些,都是有内在原因的,恰恰医生是无辜的。医者父母心,每个医生在选择这份职业的时候,都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嘉兴的急诊科室,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初具雏形开始,至今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我理想中的急诊科,对内要有一支专业的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把急诊当成终生的事业,还要将精力完全用在危重病人身上。对外要有我刚从事医生时的那种信任,能感受到接受生命重托的责任感。医生和病人,应当是同一战壕里面的战友,共同来与病魔斗争,而不是现在这般一团乱麻似的三角关系。口述曹伟中整理朱梁峰
本文刊于8月29日《江南周末》记录版
北京中科医院曝光北京看白癜风哪间医院好